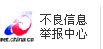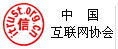说来简单,当封建领主们退出历史舞台,官员便由君主任命。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官员住在哪里?于是,朝廷就要给赴任官员提供住房。远的不说,大清朝的县太爷连同随任家属就是住在“官邸”里。这种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等到1949年之后,进城的共产党干部们在城里都没房子,他们住在哪儿就成了问题。
按级别分房子是传统
建国之初,我国就严格地按照等级制度,制定了相当细致复杂的领导干部待遇规定。比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配专车等等。住房标准自然是绕不开的问题。按照行政级别分配住房并不是舶来品。
实际上,清代官员住房就是采取近似于“福利分房”制度,原则上依照级别分配房屋。一品官给住房20间,在北京就是三进的大四合院官邸,叫做“大宅门”。
二品官给住房15间;也是三进的大四合院官邸。一二品的大员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委员或副国级官员。相当于部级干部的三品官给住房12间,相当于局级干部的四品官给住房10间,再往下五品官给住房7间。六品官给住房5间,七品官给住房4间。八品、九品官就是科级干部,给住房3间。“太阳底下无新事”,建国后也按照级别分配住房。
以上海市为例,1956年工资改革时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平米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平米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平米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平米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三级可享受160-165平米的“上等住宅公寓”;四级可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五级分得“120-135平米的新式里弄住宅”;六级可分得100-115平米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可分得80-95平米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可分得“老式立柱房屋”;如此等等。
官员们如何“合理”占多套房
“文革”期间,造反派把高干们赶进了牛棚,自己住进了花园洋房。等到拨乱反正之后,原有的领导干部住房问题再次摆在政府面前。
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中,对领导干部住房的称呼,还是“宿舍”,规定“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不得同时占用两处。调到外地工作时,应将原宿舍交回”。但是,在具体落实层面总是有很多问题。尤其是1998年房改之后,房子成了商品,成了一大笔财富,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住房腐败多有发生。
最初的问题是一名官员配多套住房。在任期间的官员住房由当地政府提供,但随着他在不同地区任职,在各个地区都有住房。一个案例显示,某省一个有29套省级干部住房的大院,其中在任省级干部住房占28%,调离干部家属住房占7%,离退休干部家属占59%,还有两套空着。而且经常出现每新来一任官员,就要搞一个书记大院的情况。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就分一套房子,调走后新的地方又给他配备了房子,并且这些房子最后都成了私人财产,这种房产的配备制度非常不合理。
领导干部调动到新地方工作自然需要住房,但是当地绝大多数的存量房已经通过房改被原来的干部买断了,调任的领导干部也不可能每在一个地方工作就买一套房子——他的工资收入也无法负担。但一个地区的领导干部总是会发生新老更替,如何解决现在领导的住房问题?这成了房改后的一个头痛问题。
官邸制能消灭“房叔”和“房婶”吗?
2001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又发布了《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级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住房面积核定及未达标、超标处理办法》,确定了各职级领导干部的购房补贴标准(按建筑面积计算):科级以下60平方米;正副科级70平方米;副处级80平方米;正处级90平方米;副司局级105平方米;正司局级120平方米;正部级220平方米,副部级190平方米。其后,各地区也制定了当地的领导干部购房补贴标准。但是住房腐败在各地却愈演愈烈。
最早是有部分领导干部利用“自有土地自建房”等多种名义,多建多占住房。后来又出现了领导干部以职权影响市场差价,低价“团购”住房。目前已经发展到领导干部违规占地、建造“官员别墅”,再加上领导干部异地任职住房中存在的混乱,使领导干部住房腐败不断升级。这些还不包括一下子就曝出几十套房子的“房叔”和“房婶”们的大手笔。今天,房子已经成为一个人一生最大的财富,各种官员住房的腐败与商品房价格一路飙升遥相呼应,极大地损害了共产党干部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实行官邸制,目标就是要在解决官员住房腐败问题的同时,也让官员们有地方住,形成“铁打的房子流水的官”的新制度。
放眼全球,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实行官邸制,美国的白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英国的唐宁街10号、法国的爱丽舍宫、日本的总理大臣官邸、韩国的青瓦台……各国官邸体现了不同的民族特色,也体现了其安保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期 作者:纪彭)